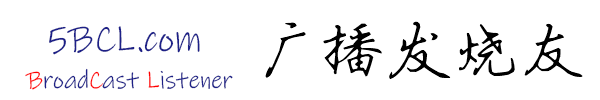作者:孟维祥
1979年,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乡村家庭。一直到90年代上初中时,村里每家都有了电视,唯独我们家因为贫困,家里除了电灯和农村的有线广播外,没有任何其他电器,成了为数不多的“例外”。
我从小就对收音机充满渴望,每当听到邻居家传出的广播声,心里就涌起一种无法言说的羡慕。那个时候,信息的传播是封闭的,收音机代表了对外界的好奇和向往。我常常幻想自己有一台收音机,能够通过它听到外面的声音,了解外面的世界,哪怕只是片刻的畅游。

初三那年,我终于决定请求母亲去跟父亲商量,让他给我买一台15元的收音机。当时15元的价格对家里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父亲一向节俭,最后他并没有答应。无奈之下,我开始动脑筋,决定自己做一台收音机。
高中的时候,我看到物理书上有收音机的电路图,同时也听同学说过有一种矿石收音机,制作起来简单且不需要电池。我兴奋不已,开始从废旧收音机中拆下零件,找来喇叭和线圈,自己捣鼓了好久。然而,当我完成所有工作,打开开关时,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寂静的空气让我感到极度的失落。那时的我,对无线电原理的理解还太浅,所学的物理知识也不足以支撑我去实现这个梦想,第一次尝试制作收音机就以失败告终。
然而,这并没有让我放弃。进入高二后,命运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转机。 那年,我在《中学生学习报》上发表了一篇英语文章,竟然收到了报社的稿费,尽管只有15元,但却让我距离梦想更近了一步。我的同桌家境较好,他是个无线电爱好者,看到我如此渴望拥有一台收音机,他慷慨地资助了我 5元钱。凑齐了这笔钱后,我终于在镇上的电器店买到了一台低档便携式收音机,它只能接收中波广播,虽然不是什么高端产品,但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满足。

不久后,我整整两个月的晚自习没吃晚饭,又攒下了些钱,终于买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短波收音机。记得那个激动的夜晚,我躲在被窝里,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莫斯科之声的广播。那一刻,我的心跳加速,仿佛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另一扇门。那个年代,信息封闭,短波收音机是普通老百姓获取国际信息最便捷、最经济的工具之一。通过它,我得以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听到不同国家的声音,那个曾经只在书本中看到的“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短波收音机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尤其是高考备考那段日子,每次学习到很晚很困时,听一会儿广播,精神便会焕发,再继续奋力学习。广播成了我的一个精神支柱,一种在艰苦环境下坚持的力量。
1997年,我考入大学,生活依然简单而朴素。家里还是没有电视,春节联欢晚会我只能通过收音机收听电视伴音,虽然没有电视画面,但每年的这段时光依然让我感到温馨和亲切。大学里,我住的宿舍楼有一个无线电爱好者,他常常通过短波电台和架设在宿舍楼顶的天线与国内外无线电爱好者进行语音通联,虽然我也很想参与,但当时一台二手短波电台的价格已经高达 5000 元,而我的月生活费只有 250 元,根本无法承受。
大学期间,除了收听国外电台的新闻外,几乎每天都收音英国 BBC 和阿美莉卡之音的英语节目,这对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提高英语听力帮助很大。
2001年大学毕业后,生活开始好转,终于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2002年底,我买了家里第一台彩电和 VCD,父亲看着电视欣喜若狂,他再也不需要到邻居家蹭电视看了。而此时,我心中一直渴望的那台根德S800短波接收机终于上市了,价格为3500元。这对于刚工作不久、月薪仅1000元的我来说,仍是天文数字。我只能每天上网看它的外形和功能介绍,心中满是渴望。

直到 2005年,我的一个澳大利亚客户从澳洲带回了一台全新的 S800,那一刻,我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后来,我开始自学无线电知识,并动手制作天线,购置了曾经只能在梦中触及的短波电台。通过这些设备,我与国内外的无线电爱好者进行了通联,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与畅快。
直到今天,毕业已24年,我仍然坚持每天收听短波广播。尽管如今通过网络也能轻松收听这些节目,但我更喜欢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听。收音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一种情怀,一种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和敬重。我怀念那段不依赖网络和电视的时光,怀念那些通过短波电波穿越时空的声音。
如果没有收音机,我或许不会选择国际贸易这条道路。正是通过它,我第一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激发了我对国际交往的兴趣。今天的我,虽然生活条件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收音机依然是我心灵的一部分,是我不变的情感寄托。